

Citation: Chen Gongdong.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Chemical Bond Theory of Linus Pauling[J]. Chemistry, 2019, 82(6): 566-575, 515.

鲍林的化学键理论的思想起源
English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Chemical Bond Theory of Linus Pauling
-
Key words:
- Chemical bond
- / Linus Pauling
- / Crystal structure
- / Quantum mechanics
- /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前期,物理学对化学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催生了物理化学、化学物理学、结构化学、射线衍射晶体学、分子生物学和量子化学等交叉学科,改变了化学的学科面貌,丰富了其理论内涵。化学键是这其中最受瞩目的交叉领域之一,它使量子物理学得以应用在“化学结合”这一古老的化学问题上,从而阐释了其本质。在化学键的问题上,美国化学家鲍林(Linus Pauling,1901~1994,图 1)的影响力十分显著,他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共振、杂化、相对电负性等化学键理论概念在化学领域深入人心,在化学与物理学和生物学产生的众多交叉学科的奠基者中均占有一席之地,他的《化学键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Chemical Bond)一书的被引用次数也常年在众多化学类著作中高居首位。作为仅有的一位独享两个不同奖项的诺奖得主,鲍林一生涉猎和成就极广,而化学键是他最核心的研究领域。在鲍林的化学键理论问世并备受关注的背后,存在化学和物理学的多种理论学说,包括路易斯化学键理论、经典结构化学、化学热力学、X射线晶体学和量子力学,它们对该理论的形成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本文将就此展开研究,探讨这几种学说在鲍林的化学键理论的形成中的重要程度。
图 1
 图 1. 1935年的鲍林。图片来源:俄勒冈州立大学档案中心(SCARC)Figure 1. Linus Pauling in 1935. Source: Special Collections and Archives Research Center (SCARC) of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图 1. 1935年的鲍林。图片来源:俄勒冈州立大学档案中心(SCARC)Figure 1. Linus Pauling in 1935. Source: Special Collections and Archives Research Center (SCARC) of Oregon State University1. 《化学键的本质》的论述
该书全名为“化学键的本质,兼论分子和晶体的结构:现代结构化学导论”(The Nature of the Chemical Bond, and the Structure of Molecules and Crystals: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Structural Chemistry),于1939年出版,是鲍林将自己在1931~1933年间发表的7篇同名系列论文的授课内容编撰而成。共振、杂化和相对电负性等概念,都在这系列论文中首次提出或受到进一步论述。
在发表该系列论文之前,鲍林在1928年春先后在《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和《化学评论》(Chemical Reviews)上发表论文,前者主张刚出现的量子力学与路易斯(G. N. Lewis,1875~1946)的电子对键(Electron-pair bond)理论对简单分子系统是相通的,尤其是海特勒(W. Heitler,1904~1981)和伦敦(F. London,1900~1954)的一级扰动法,对于碳原子的正四面体结构这一经典的结构化学问题也可以解释;后者则综述了物理学家们在1927年持续用量子力学对氢分子和氢分子离子(H2和H2+)这两种最简单的分子的平衡核间距(即键长)、系统最低能量、离解能、转动惯量和本征振动频率等性质的计算,并把这些理论计算值与实验观测值作了对比[1]。
发表这两篇论文时,鲍林刚从欧洲回到加州理工学院(CIT)不到一年。1930年底,在解决了教职问题、完善了晶体结构理论以及引进了气相电子衍射技术等工作后,鲍林再次聚焦于化学键,并在接下来的三年间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论述。
1.1 共振(Resonance)
共振是鲍林理论最核心的概念。其基本内涵是:对于a和b两个原子以及它们携带的1和2两个电子,当它们距离足够近时,如果满足a1-b2和a2-b1两种组合状态的能量都相同,那么1和2就会在a和b的原子内核之间来回高速交换,就像经典力学里的共振现象,将a和b紧密连接在一起,从而形成a-b化学键。这是共振的概念第二次被借用,海森堡(W. Heisenberg,1901~1976)在1926年解释谐振子的运动时,从经典力学借用了该概念[2],物理学家计算氢分子的时候也如此称谓;而鲍林则通过更多的分子案例使共振从量子力学概念又演化到了化学概念。
在发表于《美国化学会志》(JACS)的第一篇《化学键的本质》论文中,他总结出了六条电子对键的性质规则,规定了共振成键的条件:
(1) 电子对键的形成,需要成键的两个原子各提供一个未成对电子;
(2) 两个成键电子的自旋相反,分子的顺磁性与它们无关;
(3) 成键的两个电子不能再组成别的电子对;
(4) 一个电子对单键中,双方原子各只有一个本征函数(Eigenfunction)包含于主共振项;
(5) 成键的两个本征函数的r相同时,在成键方向上的函数值更大的一方会增大键的强度;对于给定的r,其最大值所在的方向最容易成键;
(6) 成键的两个本征函数的θ和$φ$程度相同时,r平均值更小——即能级更低——的一方会增大键的强度。
在这六条规则中,前三条是对前人(包括路易斯、海特勒和伦敦等)在化学和量子力学上的研究的归纳,而后三条则是鲍林通过量子力学语言对化学成键的论述。
共振概念基本上贯穿了鲍林这7篇论文的始终。第二篇讨论了电子对键的特殊案例单数电子键,即双方原子总共提供1个或3个电子成键;第三篇则主张电子对键(共价键)和极性键(离子键)的统一和可过渡性,认为绝大多数化学键的键型都介于共价和离子两个极端之间,其中个别化学键在外界诱导下可以连续过渡。
随着化学键研究工作的深入,鲍林对数学理论也越发倚重,他开始与韦兰(G. W. Wheland,1907~1962)、谢尔曼(J. Sherman)、魏恩鲍姆(S. Weinbaum,1898~1991)等以数学为专长的助手合作,而这样的数学化研究已经不适合发表在JACS上;与此同时,斯雷特(J. C. Slater, 1900~1976)、范伏列克(J. H. Van Vleck,1899~1980)等物理学家对化学键的研究工作也有了成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化学物理学杂志》(J. Chem. Phys.)与美国物理学联合会(AIP)于1933年成立,标志着化学物理学这一新学科正式形成[3]。鲍林《化学键的本质》的后三篇论文,都发表在了该年的《化学物理学杂志》上。对于因共振而不能只用一个电子结构式完全表达的分子,鲍林通过这三篇论文将其种类予以扩展,从苯和萘等典型个体,到可以同时存在多个电子结构的分子,再到共轭系统。在只用一种电子结构表达的化合物中,多数也存在共振现象,例如二氧化碳、羧酸、酰胺、碳酸根等,以及氮/硫杂环有机物;而共轭系统一般存在碳-碳单键和双键连续交替的结构,例如十氢萘、1, 3-丁二烯和联苯等。
朱晶等[4]指出,通过提出共振论,鲍林弱化了量子力学的数学语言,使更熟悉经典结构化学的化学家即使凭借和直觉也能自信地运用量子力学。鲍林在《化学键的本质》序言中也表达了这一观点[5]:虽然以数学性为特征的量子力学对结构化学的进展贡献甚大,但若能深入、满意地描述这一进展,仍然无需太高深的数学语言;化学家对共振论的掌握,并不难于熟悉的化学概念。
1.2 杂化(Hybridization)
根据鲍林的论述,成键双方原子的本征函数(也就是电子轨道)在特定方向上满足条件而交叠重合时,就产生了电子共振,从而形成化学键;为了形成稳定的成键电子轨道组合,原本处在s、p和d等不同能级的电子轨道会打破原有的分级,形成直线的sp、正三角形的sp2、正四面体的sp3、正方形的dsp2和正八面体的d2sp3等具有特定空间形状的组合。相比于共振成键时释放的能量,“杂化”吸收的能量很少,代价很低,因此是可行的[6]。碳原子之所以会在有机化合物中呈现正四面体构象(碳原子及其4个单键分别位于正四面体的体心及其到4个顶点的连线上),正是遵循了共振和杂化的规则,将原有的2s22px12py12pz0构象重组为2s12px12py12pz1,而这4个新的本征函数的公式的空间方向正是正四面体的4条体心-顶点连线,这就解答了物理学家对于基态碳原子只有2个单电子、却能形成4个单键的质疑。
$ \begin{array}{l} \\ \left. {\begin{array}{*{20}{r}} {{\psi _{111}} = 1/2\left( {{\rm{s}} + {{\rm{p}}_{\rm{x}}} + {{\rm{p}}_{\rm{y}}} + {{\rm{p}}_{\rm{z}}}} \right)}\\ {{{_1}_{{\rm{\bar l\bar l}}}} = 1/2\left( {{\rm{s + }}{{\rm{p}}_{\rm{x}}}{\rm{ - }}{{\rm{p}}_{\rm{y}}}{\rm{ - }}{{\rm{p}}_{\rm{z}}}} \right)}\\ {{{_{{\rm{\bar l}}}}_{1{\rm{\bar l}}}} = 1/2\left( {{\rm{s - }}{{\rm{p}}_{\rm{x}}}{\rm{ + }}{{\rm{p}}_{\rm{y}}}{\rm{ - }}{{\rm{p}}_{\rm{z}}}} \right)}\\ {{{_{{\rm{\bar l\bar l}}}}_1} = 1/2\left( {{\rm{s - }}{{\rm{p}}_{\rm{x}}}{\rm{ - }}{{\rm{p}}_{\rm{y}}}{\rm{ + }}{{\rm{p}}_{\rm{z}}}} \right)} \end{array}} \right\} \end{array} $
1.3 相对电负性(Relative electronegativity)
在第四篇中,鲍林开始用“共价键”(Covalent bond)代替了“电子对键”,并提出了相对电负性这一概念。对于双原子分子A-B的键能A:B,有经验公式:
$ {\rm{A}}:{\rm{B}} = \frac{1}{2}\{ {\rm{A}}:{\rm{A}} + {\rm{B}}:{\rm{B}}\} $
即该键能应是单质分子A2和B2的键能的平均值。实际上预测值与实验值之间总有差距Δ:
$ \Delta = {\rm{A}}:{{\rm{B}}_{{\rm{实验}}}} - {\rm{A}}:{{\rm{B}}_{{\rm{预测}}}} $
即是A和B两种化学元素的相对电负性x之差的平方:
$ \Delta = {\left( {{x_A} - {x_B}} \right)^2} $
鲍林通过卤化氢、卤素互化物和碳氢化合物等例子验证了这一论述,并将电负性最小的氢定为0.0,最大的氟定为2.0(见图 2)。其余元素的电负性都位于氢和氟之间。根据相对电负性,硼、碳和氮等电负性小的元素更容易形成共价键,因此更容易出现杂化现象;而氧和氟的电负性太大,所以不容易杂化,且易于形成离子键。
图 2
虽然相对电负性的单位是理论上罕见的“能量的平方根”,但元素在其标尺上的分布走向与元素周期表高度一致,具有很大的实用性,因此在提出之后就受到了化学家的普遍欢迎。受此影响,在《化学键的本质》系列论文中,第四篇至今的引用次数达到1120次,甚至超过了第一篇的982次,而排名第3的第五篇仅有452次[7]。
由于对化学键的共同关注,物理学家与化学家之间的互动空前频繁起来。在物理学家看来,鲍林的理论沿用了德国物理学家海特勒和伦敦1927年提出的关于氢分子电子交换的理论,又恰巧与斯雷特在同一时期发表的理论内容相近,因此被称为海特勒-伦敦-斯雷特-鲍林(H-L-S-P)理论;在化学家这边,由于鲍林关心的是英国化学家弗兰克兰(E. Frankland,1825~1899)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提出的化合价和化学键问题,因此他的理论也被称为价键(Valence bond)理论。
2. 源于物理学的思想
通过对《化学键的本质》系列论文的概览,可以看出,鲍林依靠的最基本的语境是电子成键,其次便是对量子力学的应用,而原子结构和量子理论都是物理学家开拓的;无论是构成鲍林的实验基础的X射线衍射晶体学,还是化学键理论上的竞争对手分子轨道理论,都是来自物理学。因此,本文将首先讨论来自物理学的思想。
2.1 电子与汤姆逊的原子模型
物理学家汤姆逊(J. J. Thomson,1856~1940)是公认的电子的发现者,他在1897年进行阴极射线实验时揭示了其本质,是一种电荷量不连续、质量约是氢原子的千分之一、作为原子的组分之一的粒子。汤姆逊将其命名为“微粒”(Corpuscle),并测量了它的荷质比(e/m)。“微粒”的名称在几年后让位于菲茨杰拉德(G. Fitzgerald)早已提出的“自由电子”并进一步简化为“电子”。这项研究平息了当时已经持续近20年、并被X射线的发现所激化的关于阴极射线本质的争论。Falconer[8]指出,与一般认知所不同的是,汤姆逊直到1896年受到伦琴(W. C. Röntgen,1845~1923)发现X射线的影响才开始关注阴极射线问题,因此电子的发现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然而,汤姆逊及其学派的实验物理学传统十分深厚,始终信奉实验先于理论;汤姆逊在此前20余年里一直对原子化合价和元素周期律感兴趣,并相信原子不可再分,也一直试图将化学引入物理学家的视线。最终,汤姆逊的实验还是证明了原子是可分的,这在一开始激进得有点难以接受,但实验同时证实了其他物理学家对阴极射线本质已有的“粒子说”猜测,在这一方面得到了广泛认同。
1903~1907年间,汤姆逊提出了著名的“布丁-葡萄干”原子模型,和可以用矢量箭头表示的极性化学键,并认为极性键和非极性键分属两种类型[9]。1911年卢瑟福(E. Rutherford,1871~1937)发现原子核的体积相比于原子极其微小,从此汤姆逊的原子模型不再成立,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化学键理论[10],即一个箭头表示一个电子的转移方向(如Na→Cl),一对方向相反的箭头表示一个非极性键(如Cl
$ \mathbin{\lower.3ex\hbox{$\buildrel\textstyle\rightarrow\over {\smash{\leftarrow}\vphantom{_{\vbox to.5ex{\vss}}}}$}} $ Cl)。Coffey[11]认为,汤姆逊的原子模型是用电子的“新瓶”在装贝采里乌斯(J. J. Berzelius)近一个世纪前就已提出的电二元论的“旧酒”;而简单地把极性键的理论和符号套到非极性键上,相比于汤姆逊所强调的键型区别,并不能令人满意。2.2 X射线衍射
鲍林1922年进入CIT攻读研究生后,即被化学系主席诺耶斯(A. A. Noyes,1866~1936)指派从事X射线晶体衍射(X-ray diffraction,XRD)的研究。XRD的发现及其应用于晶体结构表征而产生的X射线晶体学(X-ray crystallography,XRC),分别来自物理学家劳厄(M. von Laue,1879~1960)和布拉格父子(W. H. Bragg,1862~1942;W. L. Bragg,1890~1971)。
劳厄出自普朗克(M. Planck,1858~1947)门下,1909年加入索末菲(A. Sommerfeld,1868~1951)治下的慕尼黑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1912年初,他与即将完成学位论文的埃瓦尔德(P. P. Ewald,1888~1985)有过一次交谈,在知道晶格间距一般只有可见光波长的1/1000到1/500后,原本对晶体结构并不了解的劳厄凭借自己在光学领域的直觉,立即意识到用同一量级的波长的光照射晶格时,一定会产生衍射。索末菲等前辈对此持质疑态度,但由于尝试成本不高,因此也并未否决。劳厄在弗里德里希(W. Friedrich,1883~1968)和克尼平(P. Knipping,1883~1935)两位同事的协助下,很快搭建起了仪器设备,并对从园丁那里获得的硫酸铜样本成功获取了第一张XRD照片。同年6月,劳厄三人的工作在慕尼黑、柏林、哥廷根等地得到了汇报,并在索末菲的帮助下迅速传播开来。在理论的建立上,劳厄借用了埃瓦尔德在论文中提及的公式,通过h-k-l倒易常数提出了晶体衍射需要满足的方程。同年,英国的布拉格父子进一步证明,衍射应该归因于原子的晶格排列,并将空间中三个坐标轴方向的劳厄方程合而为一,提出了著名的布拉格公式nλ=2dsinθ(λ为X射线波长,d为晶格间距,θ为射线照射角)。这样X射线就可以用于确定晶体的晶型排列,XRC由此诞生[12]。唐有祺指出[13],直到XRD和XRC诞生后,化学家对所有类型的化学键的认识才变得更加全面和深入,尤其是离子键(如氯化钠)和金属键;而XRC对纤维等生命物质的应用,也是鲍林在30年代末开创分子生物学领域、并催动包括小布拉格在内的英美科学家在四五十年代竞相投身其中的关键原因。
1914年和1915年,劳厄和布拉格父子先后因为XRD和XRC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从而使这两门领域的研究在欧洲大陆、英国、美国和日本等地迅速展开。第二年,当时还在麻省理工学院(MIT)的诺耶斯指派自己正在德国深造的学生伯迪克(C. L. Burdick,1892~1989)穿越一战的战火,前往曼彻斯特向布拉格父子学习。当年夏天回到美国后,伯迪克先后在MIT和CIT搭建了美国的头两台XRD仪器,并完成了美国的第一份XRC研究——黄铜矿(CuFeS2)的结构。诺耶斯把队伍迁到CIT后,研究XRC的迪金森(R. G. Dickinson,1894~1945)在1920年成为学院更名改组后的第一位博士毕业生,而他正是鲍林研究生期间研究晶体结构的直接指导人[14]。到1925年博士毕业时,鲍林在合作或独立的情况下一共表征了辉钼矿(MoS2)、锡化镁(Mg2Sn)、六水合硝酸铀酰(UO2(NO3)2 ·6H2O)、铁/铝/钼氟酸铵((NH4)3(Fe,Al,Mo)F3(O,F)3)、赤铁矿(Fe2O3)、刚玉(α-Al2O3)、重晶石(BsSO4)和溴/碘碘化铯(CsI(I,Br)2)等7个系列的晶体结构的表征论文,这样优异的表现使迪金森放心地改行研究光化学。
图 3
毕业留校后的头五年,鲍林以晶体结构为主攻领域,确定了30多种晶体的结构。1929年,鲍林的《复杂离子晶体的表征原则》一文总结了5条相关的原则,又被称为“鲍林规则”,标志着鲍林成为晶体学领域的权威专家。与《化学键的本质》第四篇相似,这篇论文的被引次数目前高达1305次。鲍林主张自己在XRC领域使用的方法论是斯多噶学派的“假设与推测”方法,而不是直接演绎[15]。
当鲍林取得了这样的成绩之后,他与小布拉格(图 4)的关系由于竞争变得冷淡起来。1930年鲍林第二次前往欧洲,在曼彻斯特受到了小布拉格的冷遇,未获得任何讨论的机会。但这次鲍林却在德国遇到意外收获:染料化学公司(IG Farben)的化学家马克(H. Mark,1895~1992)及其助手维尔(R. Wierl)设计了气相电子衍射(Gaseous electron diffraction,GED)技术,但在公司里使用不上,便转让给鲍林了。该技术相比于XRD,对样品的形态和剂量的要求更低,底片曝光时间也更短[16]。借助GED,鲍林在30年代前期又确定了一大批不易结晶的气态物质的结构,进一步扩充了自己的物质结构的实验数据储备。
图 4
2.3 量子力学
在研究生期间,通过托尔曼(R. C. Tolman,1881~1948)的数学物理等课程,鲍林开始大规模接触和学习数学与物理学,并通过物理系研讨会听取众多欧洲物理学家的讲座,弥补了自己本科时期的短板。由于已经对路易斯理论产生了兴趣,鲍林对同样描述原子与电子的、由玻尔(N. Bohr,1885~1962)于1913年提出、并由索末菲作了补充的原子模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即电子沿着具有不同能量的圆形轨道围绕原子核运行。博士毕业后,鲍林于1926年初前往欧洲,在慕尼黑理论物理所跟随索末菲进行博士后研究。在欧洲,通过与泡利(W. Pauli,1900~1958)等青年理论物理学家的交流,鲍林意识到了玻尔-索末菲模型已经暴露了的不可弥补的缺陷,并在索末菲的讲授下开始接触量子力学[17]。索末菲是第一位专门开设量子力学课程的学者。这门新学科由矩阵力学和波动力学组成,前者由海森堡创立于1925年,后者由薛定谔(E. Schrödinger,1887~1961)创立于翌年,都认为电子只有最概然位置是可知的,不能同时测得其位移和动量。二者相比,矩阵力学更加抽象,而波动力学更接近经典物理,这使得大多数人选用了波动力学,但二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玻尔的冷漠是鲍林在欧洲遭遇的重大遗憾。鲍林在决定前往欧洲时也给玻尔发过申请信,但并无回音;1927年鲍林在哥本哈根与电子自旋的发现者胡德施密特(S. Goudsmit,1902~1978)共事工作了一个月,但这期间他与玻尔仅仅因为汇报工作见了一面,并且没有更多深入的沟通[18]。
图 5
在接受了量子力学后,鲍林将其应用于多原子分子和离子的物理性质预测,以及基于屏蔽常数的离子尺寸,并在索末菲的帮助下得到发表。在这期间,各国物理学家开始用量子力学对分子的平衡核间距、最低能量、离解能、转动惯量和特征振动频率等性质进行计算。在1927一年之间,丹麦的布劳(Ø. Burrau,1896~1979)用数值积分法计算了氢分子离子,美国的康顿(E. U. Condon,1902~1974)将布劳法扩展到氢分子;日本的杉浦义胜(Y. Sugiura,1895~1960)和中国的王守竞(S. C. Wang,1904~1984)紧随海特勒和伦敦之后,也对氢分子展开了计算[19]。
海特勒和伦敦在1927年上半年在苏黎世跟随薛定谔从事博士后研究,他们用一级扰动法对两个氢原子的相互作用进行了近似计算,得到系统的最低能量与平衡核间距(图 6),指出成键电子的构象彼此之间应该能够绝热迁移,即前文1.1提到的a1-b2和a2-b1两种态能量相等,并且自旋相反,否则将相互排斥无法成键[20]。相比于理论意味大于实际的“二体系统”氢分子离子,对氢分子的理论计算、尤其是考虑到电子交换的情况,是更接近化学问题、更能引起化学家的注意的,因此,该研究被科学家和科学史家普遍视为量子化学的开端。这一时期泡利不相容原则的提出和电子自旋的发现,都巩固了海特勒和伦敦的理论。
图 6
伴随着这一批研究成果的产生,物理学家对化学键的兴趣进一步增加。1931年,在鲍林发表第一篇《化学键的本质》论文的同时,曾跟随玻尔从事博士后研究的MIT的青年物理学家斯雷特也在《物理评论》发表了《多原子分子中有方向的化合价》(Directed Valence in Polyatomic Molecules)一文[21],讨论了原子内不同能级的电子本征函数的空间方向,并举出了12种分子的例子。斯雷特的工作与鲍林高度一致,这使该理论方法被科学家们称为海特勒-伦敦-斯雷特-鲍林法。
鲍林在慕尼黑和苏黎世工作期间都与海特勒和伦敦有过见面和关于化学键的密切讨论。在回到CIT之后,鲍林很快就开设了面向化学系学生讲授量子力学原理的课程,并在1935年与自己的学生威尔逊(E. B. Wilson,Jr.,1908~1992)一起将其出版为专著《量子力学导论及其在化学上的应用》(Introduction to Quantum Mechanics, with Applications to Chemistry),比《化学键的本质》还早了4年。
图 7
3. 源于化学的思想
通过上一节可以见到,化学键的物理学来源十分深厚。但鲍林仍然是一位化学家,他的理论的提出以及科学身份的保持,离不开他作为化学专业的学生所接受的理论影响和实验训练,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两位物理化学家——路易斯和诺耶斯。《化学键的本质》被鲍林献给路易斯,是这种影响的体现之一。
3.1 路易斯的化学键理论
鲍林接触到路易斯的化学键理论的时间比其他理论都早。1919年,在准备升入本科三年级时,鲍林由于母亲经营寄宿房不善导致的家境窘况而被迫辍学一年,在俄勒冈农学院化工系的帮助下,他担任了定量分析课程的讲师,以此补贴家用。由于办公地点就在学院的图书馆,因此鲍林很容易阅读到最新的《JACS》等前沿科学期刊,并接触到了朗缪尔(I. Langmuir,1881~1957)当年发表的文章《原子在分子中的排列》(The Arrangement of Electrons in Atoms and Molecules),并通过文中的介绍追溯到了路易斯三年前的论文《原子与分子》[22]。相比于鲍林在课上仍然在使用的钩子-钩眼原子模型,路易斯的共用电子对化学键理论使时年18岁、并非出身科学世家的鲍林受到了非常大的启蒙。化工系偏重生产应用、漠视讨论化学理论的氛围无法满足鲍林,这也是他决定读研深造的原因之一。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鲍林始终对路易斯所在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保持向往。在1922年的研究生申请遭到忽视后,鲍林在1929~1934年间成为伯克利的春季学期访问学者。路易斯在交流讨论中给出的意见与建议,对在这期间发表的《化学键的本质》系列论文有十分关键的帮助;对于1939年鲍林把刚面世的同名专著献给自己,路易斯无疑也是非常高兴的。
图 8
路易斯(图 8)主要研究化学热力学,但化学键带给了他同样的历史地位[23]。最早在1902年,他就产生了“立方原子”的思想:原子的每个电子层都是以原子核为共同体心的立方体,电子位于立方体的顶点上,外层电子数量等于元素所在的族数,并趋向于填满这8个位置而形成惰性气体的稳定结构。1912年,路易斯离开MIT,出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化学系主任。Simões[24]认为,截至当时,路易斯的化学键理论的历史背景已经大致形成,包括汤姆逊的原子模型、惰性气体的发现以及Abegg在1904年提出的8电子理论。翌年在《化合价与互变异构》(Valence and Tautomerism)一文中,路易斯论述了化学键的极性问题,并首次公开表达了立方原子的思想[25]。1916年,路易斯通过《原子和分子》再一次论述了极性键和立方原子。路易斯指出,尽管经典的极性与非极性物质之间差异巨大,但在环境的影响下,分子仍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过渡,而且是难以觉察的渐变;由于趋向于形成惰性气体结构,因此原子之间可以通过共享电子形成化学键,一个单键由一对共享电子组成。以卤族元素为例,单个原子(氟)最外层共有7个电子,稳定的双原子分子(碘)是两个原子共用一条棱长而形成(图 9)。
图 9
路易斯的这些论述,在《原子与分子》中被归纳为六条规则[26]:
(1) 每个原子都存在一个内核(kernel),不因任何化学变化而改变,带着过量的正电荷,过量电荷数正是该元素在周期表中所属族的序数。
(2) 原子由内核和外壳层(shell)组成,在电中性原子里,原子外层含有带负电的电子,其数量与内核所带的过量正电荷数相等,不过实际上这些电子的数量随着化学反应的不同,会在0到8之间变化。
(3) 壳层的电子数倾向于保持为偶数,尤其是8个,从而均匀分布在立方体的所有顶点上。
(4) 两个原子壳层可以彼此交叠。
(5) 电子虽被束缚在原顶点,但随时准备移动到另一个顶点。电子的运动状态取决于原子自身以及周围相连原子的本质。
(6) 两个带电粒子如果距离非常近,它们之间的电作用力将不再遵循简单的平方反比定律。
在文中,路易斯用冒号围绕元素符号以表示原子的最外层电子,这种标记法展现的电子结构被化学家们命名为“路易斯电子结构”。
路易斯同时考虑了汤姆逊和玻尔的原子模型理论,但对二者都做出了重要的改动。汤姆逊认为化学键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种类型,玻尔认为电子在轨道上围绕原子核运行。而路易斯认为两种键型只是极端情况,实际上大多数化学键都介于二者之间,这也是鲍林《化学键的本质》第三篇专门论述的话题;为了维持化学键的稳定,电子应该处于静止状态,因此它只能处在立方体的顶点上。
到目前为止,路易斯的《原子与分子》一文被引用高达1090次,可以看出它在学界中的地位。但是直到朗缪尔三年后通过《原子在分子中的分布》一文(被引用288次)提出的“化合价八隅论”(Octet Theory of Valence)将其扩展之前,路易斯并未因此获得应有的关注程度。Kohler[27]认为这是因为当时的大多数化学家不认为这是化学问题,最多只是贝采里乌斯的电二元论的一点扩展;在最能应用该理论的有机化学领域,当时也只关注于各种分子结构的确定。除了理论本身的原因,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路易斯因性格原因而与多人长期不和,也对他的理论的扩散造成了一定的困难。阎莉等[28]认为路易斯通过化学键理论对前人的继承从知识、文化和社会三个层面都与“提出经验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继承模式相符合。
3.2 经典结构化学
与现代结构化学对应的,是在原子结构发现之前已有的经典结构化学。无论是化学键、化合价、化学结构等术语,还是《化学键的本质》中重点解决的碳原子和苯的结构,都产生于经典结构化学时期[29]。1852年,弗兰克兰在研究了氮、磷、砷和锑的化合物后,首次提出“化合能力”的概念,即一种原子最多可以与多少个原子同时结合,最终在1868年将其定名为“化合价”,并在1866年首次使用了“化学键”这一术语。凯库勒(A. Kekulé,1829~1896)在1858~1865年间先后发现了碳的四价、有机物中的碳-碳键以及正六边形的苯分子结构框架,其中碳四价是凯库勒与苏格兰化学家库珀(A. S. Couper,1831~1892)各自独立发现。1861年,俄国有机化学家布特列洛夫(A. M. Butlerov,1828~1886)在德国施佩尔的会议上首次提出“化学结构”一词。1874年,荷兰人范特霍夫(J. H. van t’Hoff,1852~1911)和法国人勒贝尔(J. A. Le Bel,1847~1930)在研究旋光异构问题时,各自独立发现了碳原子的正四面体结构。至此,经典结构化学大致成型。它使化学家意识到,原子才是化学反应真正的基本单位,而并非之前杜马(J. B. Dumas,1800~1884)、李比希(J. von Liebig,1803~1873)等人主张的类型(type)或基团(radical)。
化合价和化学键与道尔顿(J. Dalton,1766~1844)的定比定律和倍比定律相互对应,描绘了原子组成分子的图景,并与同一时期由门捷列夫(D. I.Mendeleev,1834~1907)和梅耶(L. Meyer,1830~1895)发现的元素周期律一道,给出了化学元素大致的分布规律。但由于当时原子结构尚未发现,所以化学家对于化学结合问题的认识还停留在“亲合力”(affinity)的概念上,而19世纪七八十年代物理化学的兴起则令“亲合力”问题得到了众多定量的解释,并使“原子不可分”的原子论受到了能量论的冲击。
3.3 物理化学
“物理化学之父”奥斯特瓦尔德(W. Ostwald,1853~1932)借鉴了物理学的力、热、光、电的能量分类,把化学分为化学力学(后来转化为化学动力学)、热化学(或化学热力学)、光化学和电化学等分支。他聚焦于溶液和离子的研究,认为能量是物质的根本形式,并主张物理化学就是普通化学[30]。1887年他与范特霍夫和阿仑尼乌斯(S. Arrhenius,1859~1927)在莱比锡大学聚首,以及德语《物理化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physikalische Chemie)期刊的创办,标志着物理化学的正式学科化,以及化学在拉瓦锡(A. Lavoisier,1743~1794)之后向定量化和数学化迈出的又一大步。
奥斯特瓦尔德学对于美国化学在世纪交替之际摆脱落后地位的发展的影响至关重要[31]。经他调教的化学家会更加重视对数学和物理学的学习掌握,而其中美国人尤其多。在1891~1904年间,共有44名美国化学家造访了莱比锡,包括了路易斯和诺耶斯,以及多位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化学界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诺耶斯(图 10)1888年到达欧洲时,有过短暂的观望,最终选择了莱比锡大学,两年后获得博士学位。1903年,诺耶斯在MIT创立了物理化学研究实验室并担任实验室主任,使其成为又一个吸引世界各地物理化学家的圣地。诺耶斯在教学上沿袭了奥斯特瓦尔德的能量论,长期讲授化学热力学等课程;在研究方面则意识到了原子论在原子结构发现之后重新焕发的生机以及X射线晶体学广阔的发展前景,并着手为美国的X射线晶体学培养人才。
图 10
诺耶斯重视基础研究的理念与重视工业应用的MIT校方的分歧日益严重。从1917年起,诺耶斯接受天文学家、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创建者海尔(G. E. Hale,1868~1938)的邀请,前往CIT的前身特洛普(Throop)理工学院定期任教,最终在1919年将MIT实验室全部迁至特洛普学院,与海尔和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物理学家密立根(R. A. Millikan,1868~1953)一道将该学院重组并于1920年更名为CIT[32]。
在听闻CIT的存在后,即将本科毕业的鲍林也向其发出了研究生申请。诺耶斯对鲍林的兴趣和才能很赞赏,决定录取他,并让他进行XRC的研究。诺耶斯将自己刚出版的教材《化学原理》寄给鲍林,让他在本科毕业后的暑假期间完成该教材前九章的500多道习题,以达到自己“独立推导重于死记硬背”的化学教育目的。在诺耶斯的主持下,CIT化学系开设的化学课程数量少于数学和物理[33]。这样一来,学生在学业上可以分配更多的精力去学习和弥补他强调的数学和物理知识,而投在化学上的精力可以更多地集中到研究上。
就化学键问题与鲍林在同一时代竞争的分子轨道(Molecular orbital)理论源于分子光谱学(Molecular spectroscopy),由于需要阐述分子光谱而与化学键产生联系,也由于分子种类的多样性而逐渐转向化学领域。该理论主张电子只属于分子整体,而非围绕特定原子,对数学的依赖更高。两种化学键理论由于对严谨性的要求不同而被评价为“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但本质上仍然是相通的[34]。在二战后,借助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该理论逐渐受到更多的重视。关于分子轨道理论的主要奠基人马利肯(R. S. Mulliken,1896~1986)、洪特(F. Hund,1896~1997)和休克尔(E. Hückel,1896~1980)的活动历史,Simões、Karachalios、吕梦佳、沈玉龙等已有详细的研究[35~38],在此不再展开。
4. 结论
鲍林在学生时代先是接受了路易斯的化学键理论,然后在诺耶斯治下成为X射线晶体学的专家。两位前辈重视物理学的传统影响了鲍林,从而使源于物理学的X射线晶体学和量子力学成为鲍林的化学键理论的两大支柱。
化学键是化学家早已提出的概念,其背后是更加古老的化学结合问题。电子的发现与X射线在晶体学上的应用,是物理学家开始关注化学键的契机,量子理论则加剧了这一趋势。鲍林通过价键理论“翻译”[39]量子力学语言,使其与化学家所熟悉的化学键相契合,促进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对彼此领域乃至生物学等第三方领域的进一步探索,催生一批新兴的交叉学科,因此确立了自己在科学史上的地位。
偶然性是这些思想源头一路汇聚到鲍林理论的历程中十分显著的特征:发现电子时,汤姆逊投身阴极射线实验研究只有一年;伦琴因为害羞的性格始终拒绝参加同校理论物理所的活动,对应的是X射线的发现与XRD的发现间隔长达17年;鲍林了解到路易斯理论的背景是受家境所迫而暂停学业一年、担任课程讲师;鲍林赴欧学习理论物理的两年,正赶上量子理论新旧交替最繁荣的三年;鲍林首次赴欧意外受到玻尔冷遇,二次赴欧受到小布拉格冷遇,却得到电子衍射技术,等等。这些事件充满了偶然、意外、突兀乃至科学家之间的相互轻慢,但却是这段历史的真实面貌,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史料。
与此同时,化学和物理学两大学科也存在“分久必合”的趋势:重于理论的物理学的实验化,和重于实验的化学的理论化。两大学科是在拉瓦锡主导下完成的社会层面的分割,即各自建立起学院、学会、期刊和教学制度。由于拉瓦锡的化学家立场,这一分割使物理学在实验方面呈现先天性薄弱,一直到1830年代产生了能量的概念才有回转[40]。因此,从汤姆逊开始,到1927年量子物理学家们所比对的氢分子观测值的提供者,物理学在这30年间的实验化是更具有历史意义的。化学的理论化在路易斯、诺耶斯和鲍林等物理化学家手中不断推进,以至于产生了化学物理学和量子化学等一批新的交叉学科,但这并不是化学第一次受到物理学“大潮的冲刷”[41]。
从学科划分来看,鲍林的化学键理论同时拥有物理学和化学的起源,再往前追溯则是互有交叠,且以物理学居多,是一段把物理学应用于化学的历史,鲍林在其中起到了沟通桥梁的作用。但是如果考虑到实验和理论在两大学科中所占的传统比重以及两大学科的建制历史,那么汤姆逊、玻尔等物理学家对化学键理论的影响也可以视为物理学向历来以化学占优的实验的回归。
-
-
[1]
本文所引鲍林科学论文皆收录于B Kamb, L P Kamb, P J Pauling et al. eds. Linus Pauling Selected Scientific Papers, Volume I. River Edge, NJ: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c. Ltd. 2001.
-
[2]
W Heisenberg. Zeitschrift für Physik, 1926, 38(6~7): 411~426. http://qe3gw7ge4p.search.serialssolutions.com/?ctx_ver=Z39.88-2004&ctx_enc=info%3Aofi%2Fenc%3AUTF-8&rfr_id=info:sid/xueshu.baidu.com&rft_val_fmt=info:ofi/fmt:kev:mtx:journal&rft.genre=article&rft.atitle=Die%20Struktur%20der%20leichten%20Atomkerne&rft.jtitle=Zeitschrift%20F%C3%BCr%20Physik
-
[3]
H C Urey. J. Chem. Phys., 1933, 1(1): 1~2. https://www.degruyter.com/view/j/zpch
-
[4]
朱晶, 叶青.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6, 32(6): 70~75.
-
[5]
L Pauling. The Nature of the Chemical Bond.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39, vii.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16d1c71df2a7f46446944665b4caede0&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
[6]
盛根玉.化学教学, 2011, 32(11): 57~60.
-
[7]
Web of Science, 被引参考文献检索.余同. https://apps.webofknowledge.com.
-
[8]
I Falconer. Brit. J. Hist. Sci., 1987, 20(3): 241~276.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96bec32f28d47a55f98d314716d5a2a4&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
[9]
J J Thomson. The Corpuscular Theory of Matter. London, UK: A. Constable & Co., 1907.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077505a0
-
[10]
J J Thomson. Philosophical Magazine, 1914, 27: 757~789.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46092311e571aad851975f784a4197d0&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
[11]
P Coffey. Cathedrals of Sci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36~137.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07e01a21271b98613d20c7ba6c801209&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
[12]
P P Ewald ed. Fifty Years of X-Ray Diffraction. Utrecht, the Netherlands: N. V. A. Oosthoek's, 1962: 31~56.
-
[13]
唐有祺.物理, 2012, 41(11): 714~720.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WLZZ201211004.htm
-
[14]
R J Paradowski. The Structural Chemistry of Linus Pauling[D].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72: 157~177. http://ufdc.ufl.edu/AA00000383/00003
-
[15]
吕迺基.化学通报, 1981, 44(7): 439~444.
-
[16]
L J James. Naturalizing the Chemical Bond[D]. Harvard University, 2007: 256~274.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b4840eaa47b3c7ac3da199929476cc5d&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
[17]
袁振东.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6(4): 1~6.
-
[18]
T Hager. Force of Natur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5: 110~137.
-
[19]
K Gavroglu and A Simões. Neither Physics nor Chemistr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2: 12~25.
-
[20]
H Heitler and F London. Zeitschrift für Physik, 1927, 44(6~7): 455~472.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b9b400ecdc16eb0a615299496656a729&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
[21]
J C Slater. Phys. Rev., 1931, 37(3): 481~489.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54fde4d8b7e523ce0bbc0e2482a47c00&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
[22]
T Hager. Force of Nature. 55~64.
-
[23]
P Coffey. Cathedrals of Science. 38~70, 175~207.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b49e3527b1b26b5bdcb191d1a7571e11&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
[24]
A Simões. J. Comput. Quantum Chem., 2007, 28(1): 62~72.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2fde7a9b25c11eeca954438f8236450b&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
[25]
G N Lewis. J. Am. Chem. Soc., 1913, 35(10): 1448~1455.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42f8d8964bb48fe7ea245bcfa2be4a62&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
[26]
G N Lewis. J. Am. Chem. Soc., 1916, 38(4): 762~785.
-
[27]
R E Kohler. Hist. Stud. Phys. Sci., 1974, 4: 39~87.
-
[28]
阎莉, 辛翀.化学通报, 2004, 67(7): 545~550.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HXTB200407014.htm
-
[29]
W H Brock. The Norton History of Chemist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93: 241~269.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364f06c0e02b65874730a1444f96195b&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
[30]
李醒民.自然辩证法研究, 1989, 5(6): 65~70. http://zrbz.cbpt.cnki.net/WKB3/WebPublication/wkTextContent.aspx?colType=4&yt=2011&st=10
-
[31]
J W Servos. Physical Chemistry from Ostwald to Pauling. Princeton, NJ: The University Press, 1990: 46~99, 251~298. http://gateway.proquest.com/openurl?res_dat=xri:pqm&ctx_ver=Z39.88-2004&rfr_id=info:xri/sid:baidu&rft_val_fmt=info:ofi/fmt:kev:mtx:article&genre=article&jtitle=Science&atitle=Chemistry%20Regenerated.%20%28Book%20Reviews%3A%20Physical%20Chemistry%20from%20Ostwald%20to%20Pauling.%20The%20Making%20of%20a%20Science%20in%20America.%29
-
[32]
J R Goodstein. Millikan's School. New York: W. W. Norton, 1991, 76~87.
-
[33]
Interview of Linus Pauling by John L. Heilbron on 1964 March 27, Niels Bohr Library & Archives,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College Park, MD USA[OL]. www.aip.org/history-programs/niels-bohr-library/oral-histories/3448.
-
[34]
J H Van Vleck, A Sherman. Rev. Mod. Phys., 1935, 7(3): 167~228.
-
[35]
A Simões. Converging Trajectories, Diverging Traditions[D].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1993: 76~81.
-
[36]
A Karachalios. Erich Hückel (1896~1980). Heideberg, Germany: Springer, 2010.
-
[37]
吕梦佳, 白欣, 冯晓颖.化学通报, 2015, 78(9): 854~858.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HXTB201509020.htm
-
[38]
沈玉龙, 杨笑春, 舒世立等.化学通报, 2018, 81(7): 667~671.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FXJJ201820019.htm
-
[39]
B S Park. Brit. J. Hist. Sci., 1999, 32(1): 21~46.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2556aebd57d40a5e1253760ed0984a5c&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
[40]
M J Nye. From Chemical Philosophy to Theoretical Chemistry. San Francisco,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32~55.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8ba2b4db797fbaac79753e3f5132b315&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
[41]
R S Mulliken. Phys. Today, 1968, 21(4): 52~57. http://cn.bing.com/academic/profile?id=046f663f4eaaea5515cb5d1b5e2888f4&encoded=0&v=paper_preview&mkt=zh-cn
-
[1]
-
-

 扫一扫看文章
扫一扫看文章
计量
- PDF下载量: 28
- 文章访问数: 1765
- HTML全文浏览量: 5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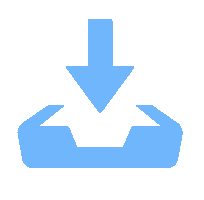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下载:
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