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itation: Zhenhua Tang, Jiamin Liu, Yihong Fu, Weinan Hu, Zhenchao Wang, Guiping Ouyang. Progress in Antitumor Activity of 3-Substituted Indole Derivatives[J]. Chemistry, 2021, 84(1): 47-52.

3-取代吲哚衍生物抗肿瘤活性研究进展
English
Progress in Antitumor Activity of 3-Substituted Indole Derivatives
-
Key words:
- 3-substitution indole
- / Heterocycle
- / Antitumor activity
-
吲哚结构普遍存在于天然及合成的药物中,生物活性多样[1]。芦卡帕利(Rucaparib)[2]、甲磺酸奥希替尼(Osimertinib)[3]、帕比司他(Panobinostat)[4]、褪黑素(Melatonin)[5](式(1))等已上市的抗肿瘤药物都是以吲哚为骨架,治疗效果良好且愈后副作用小,应用前景十分广阔。
3-取代吲哚衍生物在抗肿瘤药物的设计中占据重要地位,尤其是含氮杂环取代的化合物表现出较好抗肿瘤活性[6~10]。因此,本文按照取代杂环的类型,对近年来吡唑及吡唑啉类、二唑及三唑类、与2-位成环类等3-取代吲哚衍生物及其抗肿瘤活性进行较为系统性的综述,以期为低毒高效的抗肿瘤药物的研发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1) 1. 吡唑及吡唑啉类
Zhang等[11]设计合成了一系列3-吡唑吲哚类衍生物,并采用MTT法检测了所有化合物对4种人肿瘤细胞株的抗增殖活性。结果表明,大部分化合物对HepG-2(人肺癌细胞)、BGC823(人胃癌细胞)及BT474(人乳腺癌细胞)的细胞毒性均高于阳性对照药5-氟尿嘧啶。其中化合物1(见式(2))对BT474细胞的半数抑制浓度(IC50)为1.39μmol/L, 抑制作用是阳性对照药的52倍。此外,流式细胞术实验表明化合物2和3可将HepG-2细胞周期阻滞在S期。从构效关系看,吲哚与吡唑环均有取代的化合物的活性大于单取代化合物的,且改变吡唑环上的取代位置对细胞毒性有较大影响,而在吲哚和吡唑的N原子上连有氯代苄基时对HepG-2的细胞毒性最强。
Bhale等[12]报道了一系列含吡唑杂环的新型吲哚类衍生物,并使用SRB法测试了所有化合物对MCF-7(人乳腺癌细胞)的细胞毒性。其中化合物4对MCF-7表现出的抗增殖活性最强,GI50值(抑制细胞生长50%的药物浓度)为15.6μmol/L,而对正常的猴肾细胞的毒性极低。构效关系表明,苯环上引入吸电子基团可提高化合物对乳腺癌的抗肿瘤活性。此外,大多数化合物还表现出良好的抗炎及抗氧化活性。因此,该化合物可作为低毒高效的抗肿瘤候选药物进一步研究与开发。
Zhang等[13]以不同取代的吲哚为起始原料合成了一类含吡唑啉的吲哚衍生物。其中化合物5对HeLa(人宫颈癌细胞)、MCF-7、A549(人非小细胞肺癌)、HepG-2细胞株具有很强的细胞毒性,IC50值分别为0.21、0.29、0.26、0.31 μmol/L。该化合物可阻滞HeLa细胞G2/M期有丝分裂,并有效解除微管蛋白聚合,是一种潜在的微管蛋白聚合抑制剂(IC50=2.12μmol/L)。Chen等[14]在此基础上合成了一系列类似结构的新型抗肿瘤分子, 其中化合物6同样对HeLa、MCF-7、HepG-2细胞具有很强的抗增殖活性,但表现出比化合物5更好的微管蛋白抑制活性(IC50=1.6μmol/L),且化合物6对正常人肾上皮细胞细胞无毒性。此外该化合物对HeLa细胞异种移植小鼠的肿瘤抑制率可高达61.52%,但无任何正常组织受损。
Shu等[15]以拓扑异构酶Ⅰ为靶标,设计合成了一系列新型吡唑啉-吲哚类衍生物。其中化合物7可抑制拓扑异构酶Ⅰ与DNA形成复合物,导致肿瘤细胞发生凋亡,并表现出比喜树碱更强的拓扑异构酶抑制活性。与经典的嵌入模式不同,化合物7是通过吡唑环上的萘环与拓扑异构酶Ⅰ的π-π堆积作用与复合物结合而抑制拓扑异构酶Ⅰ的活性。活性-结构关系的研究结果显示,吡唑环上引入给电子基团可增强化合物的抑制作用。
(2) 综上所述,该类化合物由于吡唑或吡唑啉的引入提高了吲哚对HeLa、MCF-7及HepG-2等肿瘤细胞的抗增殖活性与选择性。另外,在吡唑或吡唑啉环N原子上构建羰基、苯环、萘环等结构有利于增加化合物的细胞毒性。
2. 二唑及三唑类
Kumar等[16]设计合成了一系列含1, 3, 4-三唑环的吲哚衍生物。其中化合物8、9、10(见式(3))分别对PaCa-2(人胰腺癌细胞)、MCF-7、PC-3(人前列腺癌细胞)具有选择性细胞毒性(IC50分别为0.8、1.6、4 μmol/L)。构效关系分析显示,在1, 3, 4-三唑环上引入哌啶基增强了化合物对MCF-7细胞的细胞毒性及选择性;而苯甲氧基、4-氟苯基的引入进一步提高了1, 3, 4-三唑吲哚衍生物的抗增殖活性及对PC-3细胞的选择性毒性。
Tantak等[17]以几种已报道的天然生物碱及细胞毒性剂为先导化合物,采用活性拼接设计合成了一系列1, 3, 4-噁二唑类衍生物。其中化合物11对HeLa细胞展现出极强的抑制作用,IC50值低于0.001μmol/L,是对照药多柔比星的900倍(0.9±0.04μmol/L)。该化合物还可诱导MDA-MB-231(人乳腺癌细胞)的凋亡。相比于未取代的吲哚环,在吲哚的5-位引入甲氧基或卤素基团可显著增强化合物的抗增殖活性。
Shirinzadeh等[18]对褪黑素的结构进行修饰与改造,设计合成了一系列含有噻二唑的吲哚衍生物。其中化合物12对CHO-K1(仓鼠卵巢细胞)具有显著的抗增殖作用,IC50值小于10μmol/L。化合物12的结构与舒尼替尼相似,作用方式可能为抑制酪氨酸激酶的活性,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此外,该化合物还表现出良好的自由基(DPPH)清除活性。
Kamath等[19]开发了一种绿色、高效的方法合成了一系列含噁二唑的新型双吲哚衍生物。其中化合物13对MCF-7细胞具有较强的选择性毒性,IC50为8.45μmol/L。进一步机制研究表明,化合物13可引发MCF-7细胞的G1期细胞周期阻滞,并通过激活caspase-2、caspase-9(半胱氨酸蛋白)及抑制抗凋亡蛋白Bcl-2的活性诱发该细胞程序性死亡。另外,化合物13还可显著抑制MCF-7细胞的转移。从活性看,吲哚与噁二唑环之间无亚甲基的化合物细胞毒性更高。
除化学合成外,近年来也报道了大量从海洋生物中分离提取的天然吲哚类生物碱具有多种生物活性[20]。Topsentin是一类从海绵体Spongosorites genitrix中分离得到的天然双吲哚生物碱,包括Topsentin A、Topsentin B1等结构,具有抗肿瘤、抗炎等生物活性[21]。Naaz等[22]将Topsentin中的咪唑环替换为1, 2, 4-三唑及1, 3, 4-噁二唑基团,设计合成了一系列Topsentin生物碱类似物,其中化合物14、15、16对黑色素瘤、结肠癌细胞和乳腺癌细胞株均表现出较好的抗增值活性(IC50值分别为2.42、3.06、3.30 μmol/L),且对MCF-7细胞呈现出比对照药阿霉素(IC50=6.31μmol/L)更强的作用。另外,化合物14还可将MCF-7细胞阻滞于G0/G1期,并抑制该细胞的微管蛋白聚合。构效关系研究表明,1, 3, 4-噁二唑类衍生物较1, 2, 4-三唑类衍生物活性更好,苯环上卤素基团的引入进一步提高了抗肿瘤活性,对活性的影响依次为2-F>3-Br>4-NO2>3-Cl。
(3) 综上所述,此类3-取代吲哚衍生物多为从海洋生物中分离得到的天然生物碱,或以天然生物碱为模板进行的结构修饰与改造。二唑及三唑环的引入使吲哚的抗增殖活性及选择性都有所提高,且大多表现出优于对照药的抗肿瘤活性,是有效的细胞毒性剂。
3. 2, 3-位成环类
Peng等[23]对白叶藤等生物碱进行结构改造,合成了一类新型吲哚[2, 3-b]喹啉衍生物。其中带有甲氧基的化合物17(见式(4))对MV4-11(人白血病细胞)及化合物18对HCT-116(人结直肠癌细胞)具有很高的抗增殖活性与选择性(IC50分别为0.12和1.70 μmol/L),相比于抗肿瘤药物顺铂的作用更强(IC50相应为2.82、8.5 μmol/L)。紫外吸收实验显示,化合物17发挥抗增殖作用可能是通过插层模式与肿瘤细胞DNA紧密地结合,并抑制拓扑异构酶Ⅱ的活性。从构效看,在喹啉环上引入甲氧基、氨基链有利于提高化合物对MV4-11细胞的选择性与活性。
Chaniyara等[24]以多个药效基团为模板,利用活性拼接原理设计合成了一类新型吲哚衍生物。体外抗增殖实验表明,取代基的大小对活性有较大影响,吲哚N原子被甲基取代(化合物19)时对人急性淋巴白血病细胞CCRF-CEM的细胞毒性最大(IC50为0.04μmol/L),而且其对MX-1(人乳腺癌细胞)异种移植小鼠的缓解率高达99%;化合物20在HT-29(人结肠癌细胞)异种移植模型中的抑制作用强于抗结肠癌药物伊立替康,但对正常细胞的影响甚微。这些化合物抗肿瘤的作用机制包括诱导DNA链间交联、阻断DNA复制、诱导肿瘤细胞凋亡、抑制拓扑异构酶Ⅰ和Ⅱ的活性、阻滞细胞周期等。值得一提的是,该系列化合物对长春新碱及阿霉素无交叉耐药性。
Devambatla等[25]设计合成了一系列嘧啶并吲哚类衍生物。其中化合物21和22对MDA-MB-4359(人黑色素瘤细胞)、SK-OV-3(人卵巢癌细胞)、HeLa细胞具有较好的抗增殖活性。此类化合物作用于微管蛋白时可绕过P-糖蛋白和bIII-微管蛋白位点,不产生多药耐药性,是一种有效的靶向微管蛋白解除剂。构效关系研究表明,位于嘧啶环两个N之间的取代基的大小对抑制微管蛋白的活性及细胞毒性均有有较大的影响,氨基及甲基取代的衍生物的活性优于未取代的化合物。
Patil等[26]基于靶点设计合成了一系列吡啶并吲哚类衍生物。其中,化合物23对非小细胞肺癌、转移性结肠癌、前列腺癌及三阴性乳腺癌等多种肿瘤细胞均表现出很强的抗增殖活性及选择性。构效关系揭示吲哚5-位取代基为甲氧基时抗肿瘤活性最佳。另有分子对接实验表明,化合物23能与MDM2(原癌基因)有效结合,破坏p53(野生型抑癌基因)与MDM2的相互作用,恢复p53的活性,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是潜在的MDM2抑制剂。
Jorda等[27]通过一步反应合成了一系列galeterone(晚期前列腺癌药物)类似物。相较于其他杂环衍生物,吲哚并吡啶的化合物24对人前列腺癌细胞22Rv1-ARE14及VCaP的抗增殖活性均最高,GI50值均小于0.2μmol/L,但当吲哚1-位接甲基时活性最低。该化合物抗肿瘤的机制主要是以剂量依赖的方式降低AR(雄激素受体)调控的转录活性、抑制Nkx3.1(转录因子同源蛋白)及人前列腺肿瘤细胞22Rv1-ARE14和VCaP中前列腺特异性抗原的表达。此外,化合物24与AR的结合能力要比晚期前列腺癌药物Galeterone更强。
(4) 综上所述,2, 3-位成环类吲哚衍生物数量较多,多为吲哚并六元含氮杂环,在此类化合物上引入甲氧基可导致抗肿瘤活性的改变。此外,该类化合物抗肿瘤的作用方式多样,治愈率高,耐药性低,毒副作用也小,是潜在的高效低毒的抗肿瘤药物。
4. 其他类
Spanò等[28]合成了一类含噻吩结构的Nortopsentin生物碱类似物,其中,化合物25(见式(5))对MCF-7细胞抗增殖活性最强。进一步机制研究表明,化合物25可诱导MCF-7细胞向早期凋亡转化,但不会引发坏死。此外,化合物25还可调控细胞周期,将MCF-7细胞阻滞于G2/M期。Lafayette等[29]也在3-位引入噻吩杂环合成了一类新型吲哚衍生物, 其中,化合物26抗人乳腺癌细胞T47D增殖的作用强于对照药阿霉素(IC50值分别为1.93及4.61 μmol/L)。化合物27可与白血病细胞HL60、K562的碱基对形成非常稳定的氢键,发生非共价结合,干扰该肿瘤细胞的复制。
Gao等[30]合成了一类含吡啶并嘧啶杂环的吲哚类衍生物。构效关系分析得出,苯环上连有吸电子基的化合物活性较含给电子基的要高,其中对位为氯的化合物28对HepG-2细胞具有有很强的细胞毒性,但对正常细胞影响很小。该化合物通过抑制AKT和ERK1/2信号通路;上调caspase-3、caspase-8及促凋亡蛋白Bax的表达,同时下调Bcl-2的表达,诱导HepG-2细胞发生凋亡,而且化合物28还可将HepG-2细胞阻滞于S和G2/M期、并有效抑制该肿瘤细胞皮下异种移植物的生长。该化合物是安全有效的抗肝癌候选药物。
Neochoritis等[31]通过分子对接以及相应的药效团研究设计合成了一系列双吲哚类衍生物。其中,化合物29与MDM2、MDMX均有极强的亲和力与结合力,可抑制p53-MDM2及p53-MDMX之间的相互作用,恢复p53的抗肿瘤活性,是一种高效的双拮抗剂。双吲哚结构中的两个苯环可以提供额外的与p53Val93的疏水相互作用,从而达到更好的抑制效果。这一类双吲哚衍生物可作为候选药物进一步研究与开发。
Cascioferro等[32]以不同取代的吲哚为原料,合成了一系列含有咪唑并噻二唑的吲哚类衍生物。体外抗增殖实验显示,化合物30对SUIT-2、Capan-1、Panc-1三种胰腺导管腺癌细胞均展现出较好的抗增殖活性,IC50分别为5.5、5.11、5.18 μmol/L。卤素及甲氧基的引入有利于细胞毒性的增强。此外,细胞划痕实验表明,化合物30比晚期胰腺癌药物吉西他滨更有效地减少SUIT-2及Capan-1细胞的迁移率。
Zhao等[33]利用计算机模拟对接设计合成了一类含噻吩并嘧啶结构的吲哚衍生物。分子对接结果表明,在丙烯酰胺处引入卤素和烷基削弱了化合物与非目标蛋白的结合能力,因此化合物对正常细胞毒性和副作用大大降低。其中化合物31显著抑制EGFRL858R与EGFRT790M蛋白的突变,是一种高选择性的EGFR抑制剂。此外,化合物31能有效抑制A549及HeLa细胞的生长(IC50值分别为0.057及0.104 μmol/L),且对H1975细胞的抑制率高达99%以上,IC50为0.916μmol/L。
(5) 综上所述,此类吲哚衍生物中3-位所含杂环取代基结构多样,包括噻吩等五元杂环、吡啶并嘧啶等双杂环,为抗肿瘤药物设计提供了更多多元化的选择;同时该类化合物具有广泛的抗肿瘤活性,通过多种机制达到显著的肿瘤细胞毒性,具有广阔的开发前景。
5. 结语
在吲哚的3-位构建吡唑、噻二唑、三唑等不同的杂环,进一步提高了吲哚的抗肿瘤活性。与单个药效团相比,多个杂环结构的合理叠加增强了分子与受体结合的强度与选择性。噻吩及1, 3, 4-三唑等杂环的引入提高了吲哚对HepG-2、MCF-7及HeLa等肿瘤细胞的细胞毒性与选择性,部分化合物还表现出比一些临床常用抗肿瘤药物更高的活性。另外,杂环-吲哚类化合物上取代基的类型及位置的不同对抗肿瘤活性也有重要的影响。例如,氨基烷基链可增强化合物与DNA链结合的活性和选择性,在吡唑-吲哚杂化物的吲哚或吡唑N位上接卤代苄基等吸电子基也可增强活性等。总的来说,3-取代吲哚衍生物可通过诱导细胞凋亡、阻滞细胞周期、抑制拓扑异构酶的活性、抑制微管蛋白聚合、调控相关蛋白与信号通路的表达、与DNA结合等作用机制发挥抗肿瘤活性。3-位取代吲哚衍生物是一种活性优良的高效抗肿瘤药物分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但在临床应用上仍存在一些缺陷,如毒副作用大、易复发、耐药性高等。在今后的研究中应更多关注于对3-位侧链结构的优化改造,以提高对肿瘤细胞的选择性,增强与肿瘤细胞的特异性结合的能力,降低对机体的损伤并减少耐药性,进而开发出低毒高效的抗肿瘤药物。
-
-
[1]
Singh T P, Singh O M. Mini-Rev. Med. Chem., 2018, 18(1): 9~25.
-
[2]
Dal Molin G Z, Omatsu K, Sood A K, et al. Ther. Adv. Med. Oncol., 2018, 10: 1~13. doi: 10.1177/1758835918778483
-
[3]
Van Veggel B, Madeira R S J F V, Hashemi S M S, et al. Lung Cancer, 2020, 141: 9~13. doi: 10.1016/j.lungcan.2019.12.013
-
[4]
Dias J N R, Aguiar S I, Pereira D M, et al. Oncotarget, 2018, 9(47): 28586~28598. doi: 10.18632/oncotarget.25580
-
[5]
Cheng Y, Cai L, Jiang P, et al. Eur. J. Pharm., 2013, 715(1-3): 219~229. doi: 10.1016/j.ejphar.2013.05.017
-
[6]
Dadashpour S, Emami S. Eur. J. Med. Chem., 2018, 150: 9~29. doi: 10.1016/j.ejmech.2018.02.065
-
[7]
Rosales P F, Bordin G S, Gower A E, et al. Fitoterapia, 2020, 143: 104558. doi: 10.1016/j.fitote.2020.104558
-
[8]
Kumar D, Sharma S, Kalra S, et al. Curr. Drug Targets, 2020: 115327.
-
[9]
Chen F Y, Li X, Zhu H P, et al. Front. Pharmacol., 2020, 11: 280. doi: 10.3389/fphar.2020.00280
-
[10]
Wan Y, Li Y, Yan C, et al. Eur. J. Med. Chem., 2019, 183: 111691. doi: 10.1016/j.ejmech.2019.111691
-
[11]
Zhang D T, Wang G T, Zhao G L, et al. Eur. J. Med. Chem., 2011, 46(12): 5868~5877. doi: 10.1016/j.ejmech.2011.09.049
-
[12]
Bhale P S, Bandgar B P, Dongare S B, et al. Phosphorus Sulfur, 2019, 194(8): 843~849. doi: 10.1080/10426507.2019.1565760
-
[13]
Zhang Y L, Qin Y J, Tang D J, et al. ChemMedChem, 2016, 11(13): 1446~1458. doi: 10.1002/cmdc.201600137
-
[14]
Chen K, Zhang Y L, Fan J, et al. Eur. J. Med. Chem., 2018, 156: 722~737. doi: 10.1016/j.ejmech.2018.07.044
-
[15]
Shu B, Yu Q, Hu D X, et al. Bioorg. Med. Chem. Lett., 2020, 30(4): 126925. doi: 10.1016/j.bmcl.2019.126925
-
[16]
Kumar D, Narayanam M K, Chang K H, et al. Chem. Biol. Drug Design, 2011, 77(3): 182~188. doi: 10.1111/j.1747-0285.2010.01051.x
-
[17]
Tantak M P, Kumar A, Noel B, et al. ChemMedChem, 2013, 8(9): 1468~1474. doi: 10.1002/cmdc.201300221
-
[18]
Shirinzadeh H, Ince E, Westwell A D, et al. J. Enzyme Inhib. Med. Chem., 2016, 31(6): 1312~1321. doi: 10.3109/14756366.2015.1132209
-
[19]
Kamath P R, Joseph M M, Abdul Salam A A, et al. J. Biochem. Mol. Toxicol., 2017, 31(11): e21962.
-
[20]
Netz N, Opatz T. Marine Drugs, 2015, 13(8): 4814~4914. doi: 10.3390/md13084814
-
[21]
Golantsov N E, Festa A A, Karchava A V, et al. Chem. Heter. Compd., 2013, 49(2): 203~225. doi: 10.1007/s10593-013-1238-9
-
[22]
Naaz F, Ahmad F, Lone B A, et al. Bioorg. Chem., 2020, 95: 103519. doi: 10.1016/j.bioorg.2019.103519
-
[23]
Peng W, Switalska M, Wang L, et al. Eur. J. Med. Chem., 2012, 58: 441~451. doi: 10.1016/j.ejmech.2012.10.023
-
[24]
Chaniyara R, Tala S, Chen C W, et al. J. Med. Chem., 2013, 56(4): 1544~1563. doi: 10.1021/jm301788a
-
[25]
Devambatla R K V, Li W, Zaware N, et al. Bioorg. Med. Chem. Lett., 2017, 27(15): 3423~3430. doi: 10.1016/j.bmcl.2017.05.085
-
[26]
Patil S A, Addo J K, Deokar H, et al. Drug Design., 2017, 6(1): 143.
-
[27]
Jorda R, Reznickova E, Kielczewska U, et al. Eur. J. Med. Chem., 2019, 179: 483~492. doi: 10.1016/j.ejmech.2019.06.040
-
[28]
Spano V, Attanzio A, Cascioferro S, et al. Marine Drugs, 2016, 14(12): 226. doi: 10.3390/md14120226
-
[29]
Lafayette E A, De Almeida S M V, Santos R V C, et al. Eur. J. Med. Chem., 2017, 136: 511~522. doi: 10.1016/j.ejmech.2017.05.012
-
[30]
Gao X, Cen L, Li F, et al. Biochem. Biophys. Res. Commun., 2018, 505(3): 761~767. doi: 10.1016/j.bbrc.2018.09.120
-
[31]
Neochoritis C G, Wang K, Estrada-Ortiz N, et al. Bioorg. Med. Chem. Lett., 2015, 25(24): 5661~5666. doi: 10.1016/j.bmcl.2015.11.019
-
[32]
Cascioferro S, Petri G L, Parrino B, et al. Molecules, 2020, 25(2): 329. doi: 10.3390/molecules25020329
-
[33]
Zhao B, Zhao C, Hu X, et al. Eur. J. Med. Chem., 2020, 185: 111809. doi: 10.1016/j.ejmech.2019.111809
-
[1]
-

 扫一扫看文章
扫一扫看文章
计量
- PDF下载量: 41
- 文章访问数: 2332
- HTML全文浏览量: 7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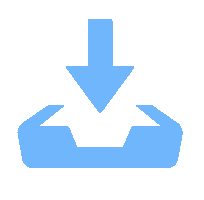 下载:
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