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itation: ZHU De-Cheng, CHEN Yi-Xin, JI Chong-Xing, ZHU Xian-Yu, LI De-Cheng. Effect of Pickling Treatment on Structure, Morphology and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 of NaEuTiO4[J]. Chinese Journal of Inorganic Chemistry, 2020, 36(9): 1690-1700. doi: 10.11862/CJIC.2020.201

酸洗处理对NaEuTiO4的结构、形貌以及电化学性能影响
English
Effect of Pickling Treatment on Structure, Morphology and Electrochemical Performance of NaEuTiO4
-
Key words:
- lithium-ion battery
- / anode material
- / rare earth
- / titanium based
- / pickling
-
0. 引言
在过去的30年中,锂离子电池已广泛应用于便携式电子设备当中,并在近年来扩展到大型储能电站和电动汽车(例如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等应用领域[1-3]。但是,锂离子电池在这些新的应用场景中需要在能量密度、安全性和使用寿命上满足更高的要求。石墨类碳材料作为最常见的商业化的负极材料,其较低的嵌锂电位(大约0.1 V)会导致电池负极表面析锂现象的产生,从而给电池带来安全上的隐患;同时,石墨材料较低的比容量也限制了电池能量密度的进一步提高[4-7]。因此,有必要研究和开发替代石墨的新型负极材料。
被称为“零应变”的Li4Ti5O12作为新型的负极材料,已经成功地在锂离子电池中得到了应用。利用钛酸锂负极材料制成的锂离子电池表现出了优异的循环性能和良好的安全性能[8]。遗憾的是,与石墨相比,Li4Ti5O12的高嵌锂电势(1.55 V vs Li/Li+),以及低可逆容量严重地降低了电池的能量密度[9-10],进而限制了钛酸锂负极材料在锂离子电池中的广泛应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人们又研究和开发了许多嵌锂电位在1 V左右的钛基氧化物材料,例如Li(V0.5Ti0.5)S2[11]、LiTiS2[12]和Na2Li2Ti6O14[13-14]等,但是这些材料与现有负极材料相比仍然缺乏足够的竞争力。
最近,人们发现具有层状钙钛矿结构的LiEuTiO4(LETO)具有良好的可逆脱/嵌锂行为[15-18]。它的脱/嵌锂电位在0.8 V左右(相对金属锂负极),这个电位可以有效避免脱/嵌锂过程中的析锂问题,从而改善电池的安全特性。同时,它的可逆容量在200 mAh·g-1以上,嵌锂电位的降低以及可逆容量的提高使得LETO比钛酸锂负极具有更好的能量密度,应用前景更加广泛[17]。更让人们感兴趣的是,LETO具有与其它负极材料截然不同的层状钙钛矿结构,而且它的主要氧化还原电对是Eu2+/Eu3+,而不是Ti3+/Ti4+。这些特点可能让更多的稀土钛酸盐成为潜在的新型负极材料。因此,深入研究基于稀土钛基氧化物的电化学行为对于设计和制备新型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当前,具有良好充放电特性的LETO常以NaEuTiO4(NETO)为母本材料,通过离子交换方法获得[15-17, 19]。一般说来,能够进行离子交换的层状钙钛矿主要有3类:Dion-Jacobson(D-J)类[20-21]、Ruddlesden -Popper(R-P)类[22-23]和Aurivillius类[24],这些材料由于具有独特的光、电和磁特性而受到广泛的研究。NETO属于R-P类的层状钙钛矿结构,是NaLnTiO4中的一种。研究结果表明NaLnTiO4化合物的晶体结构与镧系稀土离子种类密切相关,当Ln=La~Nd时,理想的八面体TiO6为四方对称型结晶。另一方面,随着TiO6的相互倾斜,NaLnTiO4(Ln=Sm~Lu)化合物以正交对称的方式结晶,从而使八面体TiO6与Na+之间的相互作用强于四方对称型。对于NaLnTiO4中钠离子与其他离子交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结构上的变化,性能研究也多集中在磁性和光学方面,对于钠离子与其他离子交换后所获得材料的电化学性能研究还不是十分深入。Masaki研究了NaLnTiO4(Ln=Sm,Eu,Gd)的磁性质[25];Song研究了Na+和Li+交换后在晶体结构和磁性方面的变化[15];Nishimoto通过将NaLaTiO4、LiLnTiO4和KLaTiO4浸泡在稀盐酸中,发现水分子和氢离子可以嵌入到母本化合物中,然而对于新形成的化合物的电化学性能没有深入研究[26]。
我们通过溶胶凝胶法合成了层状钙钛矿结构的NETO,并利用稀硝酸对其进行了酸洗处理。我们发现,NETO中的钠离子可以跟稀酸中的氢离子发生离子交换。交换后得到的化合物HEuTiO4可以在电池中通过电化学反应的方式转化为LiEuTiO4 (LETO),这种转化得到的LETO与文献中通过熔盐法交换得到的LETO一样具有良好的可逆脱/嵌锂行为。
1. 实验部分
1.1 样品的制备
本实验使用的试剂均为购买后直接使用,无后续处理过程。
将碳酸钠(AR)、三氧化二铕(99.99%)以1.3:1的物质的量之比混合在2 mol·L-1 20 mL的稀硝酸中,在80 ℃下搅拌以除去过量的硝酸,然后与10 mL去离子水一起搅拌以获得溶液A。在10 mL乙醇和10 mL冰醋酸的混合物中加入一定量的钛酸四丁酯(AR),搅拌得到溶液B。然后将溶液B逐滴加入溶液A中,并剧烈搅拌得到溶液C。溶液C在烘箱中70 ℃干燥24 h后继续在120 ℃下干燥24 h,获得白色干燥凝胶。将凝胶置于马弗炉中于500 ℃燃烧2 h,然后在900 ℃煅烧7 h,以获得前驱体NaEuTiO4。然后取0.574 g NaEuTiO4溶于50 mL 0.5 mol·L-1稀硝酸中,分别搅拌1、3、6、12和24 h。将下层沉淀物过滤并用去离子水和乙醇重复洗涤几次,直到pH=7。最后在70 ℃的烘箱中干燥12 h,得到酸处理的NaEuTiO4。根据酸处理时间将不同样品分别命名为NETO-x(x=1、3、6、12、24 h)。为了进行比较,将未经酸处理的NaEuTiO4称为NETO。
1.2 样品的结构分析和表征
将样品用乙醇超声分散后滴在硅片上,干燥后,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SEM,SU801日本)在测试电压10 kV和测试电流10 mA条件下来观察材料的微观结构,并在15 kV测试电压下进行能谱分析(EDS)。通过透射电子显微镜(TEM,FEI-Tecnai G20 STWIN,美国)在200 kV的加速电压下观察样品的包覆情况和材料晶体结构变化,进一步观察和研究材料的微观形貌。通过表面积及孔径分析仪(TristarⅡ 3020 Micromeritics,美国)分析样品包覆前后的比表面积变化情况。通过电感耦合等离子发射光谱仪(ICP,OPTIMA 8000,美国)和固体核磁(NMR,AVANCEⅢ/WB-400,瑞士)在400 MHz下测试1H谱来验证是否交换成功。
样品的晶体结构通过X射线衍射分析(XRD,Bruker D8 advance,德国)测试得到。以Cu Kα为辐射源,波长λ=0.154 056 nm,工作电压为40 kV,工作电流为40 mA,扫描范围为10°~80°,测试速率为10 (°)·min-1。通过X射线光电子能谱(XPS,ESCALAB 250Xi,美国)研究酸处理对材料晶体结构的影响,以C1s的284.8 eV为标准测试能谱,测试电压为10 kV,测试电流为10 mA。
1.3 电池组装以及性能测试
将活性材料、Super-P(导电碳)和粘结剂(NaC- MC,国药沪试,CP)按照质量比7:2:1研磨混合后,加入少量水,搅拌8 h。将所得到的浆料用自动涂膜剂均匀涂抹在铜箔的表面。先将铜箔放置在50 ℃烘箱中干燥1 h,然后转移至110 ℃真空干燥箱中干燥12 h,切片,得到极片。
在氩气氛围的手套箱中,以1 mol·L-1 LiPF6的碳酸二乙酯+碳酸乙烯酯溶液(1:1,V/V)作为电解液,将极片、隔膜(Celgard 2400)和金属锂片(15 mm× 1 mm)组装成CR 2016型扣式电池。
新制的电池静置6 h后,转移至Land CT 2001 A (武汉蓝电)在恒温下(25 ℃)进行充放电测试以及倍率循环测试。电压测试区间为0.01~3.0 V,电流密度为100 mA·g-1。电化学循环伏安测试(CV)在电化学工作站(辰华CHI660D武汉)上进行,扫描速率为0.1 mV·s-1。
2. 结果与讨论
2.1 结构和形貌表征
图 1给出了未处理的NETO和经不同时间酸洗处理后的NETO-x样品XRD图。如图 1所示,NETO中的所有强衍射峰均很好地与NaEuTiO4的标准峰(PDF No.47-0004)对应,且没有观察到其他峰,表明我们制备的NETO具有非常好的纯度和结晶度。将NETO用HNO3处理1 h后,属于NETO的峰强度明显降低,同时在图 1和图 2中的“●”所示位置出现了一些新的峰,表现出两相共存的特点;随着酸洗时间的增加,属于NETO的XRD峰的强度逐渐减少,而新峰的强度增加表明NETO的晶体结构正逐渐向新相转变。Nishimoto的研究表明[26],用稀盐酸处理NaLnTiO4时,Na+可以和H+完全交换。Akimoto等[27]也采用0.5 mol·L-1 HCl处理Na2Ti3O7得到H2Ti12O25微米颗粒,因此我们推测酸处理中也发生了Na+与H+的交换。酸处理6 h后,不再有新峰的出现,同时原有NETO的衍射峰也基本消失,暗示着Na+已经与H+完全交换,可能形成HEuTiO4(HETO)。
图 1
图 2
此外,如图 2所示,当酸洗时间增加时,标记峰的中心位置向高角度方向移动,表明样品发生了体积收缩。众所周知,H+的离子半径小于Na+的离子半径,所以我们认为样品体积收缩是因为样品中的Na+被H+取代。
我们用JADE计算出了NETO和NETO-x在不同的酸洗时间下的晶格参数,结果如图 3所示。原始NETO的晶格参数分别为1.255 0、0.533 2和0.533 0 nm,与文献报道基本一致[28]。酸洗处理1 h后,晶格参数a最初降低至1.248 6 nm,然后当处理时间增加至3 h,a逐渐增加至1.260 0 nm,酸洗时间6、12和24 h后的a分别为1.261 5、1.262 5和1.262 7 nm。同时,当处理时间为1 h时,晶格参数b最初增至0.534 6 nm,然后当处理时间增加至3、6、12和24 h后,b逐渐减小至0.533 2、0.532 3、0.532 2和0.532 0 nm。晶格参数c和V随着浸泡时间的增加而连续减小。这些结果表明,在离子交换过程中,短轴c方向晶面间距随着用H+不断代替Na+而持续减小,而长轴a方向和短轴b方向的原子距离的变化相当复杂。NETO具有正交晶格的Ruddlesden-Popper结构,属于Pbcm(57)空间群[16-17, 28],在TiO2的任一侧上,Na2O2岩盐层与Eu2O2岩层交替出现。我们认为上述现象的发生是因为当HNO3中的H+和NETO中的Na+之间发生离子交换反应时,NETO的交替钙钛矿层的框架会保留,而由于H+的离子半径比Na+小,导致Eu-O岩盐配位层和TiO2之间产生了较大的扭曲,从而导致晶格常数上发生较为复杂的变化。在后续的工作中会研究其具体的结构变化及原因。
图 3
为了研究酸处理对NETO晶粒形貌的影响,我们对其进行了SEM和TEM测试,实验结果如图 4和图 5所示。由图 4可知,NETO的晶粒呈现出典型的纳米片形态,晶粒结晶完整,形状较为规则,表面光滑,大小在2~5 μm之间,厚度大约500 nm。NETO晶粒在HNO3中酸洗不同的时间后,其形状变得不规则,并且在晶粒上出现许多裂纹,裂纹数量随着处理时间的增加而增加。此外,当处理时间为12 h时,裂纹的长度可达1.15 μm。当处理时间为24 h时,如图 5所示,晶粒的结晶度受到严重破坏。同时,如表 1所示,当处理时间从1 h增加至6 h时,样品的比表面积先不断增加,然后急剧减小,这是由于表面小晶粒的溶解。
图 4
图 5
表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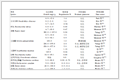 表 1 NETO酸处理样品的初始充放电容量、初始库仑效率和比表面积Table 1. Initial charge-discharge capacities, initial coulombic efficiencies as well as the specific surface area of NETO-x samples
表 1 NETO酸处理样品的初始充放电容量、初始库仑效率和比表面积Table 1. Initial charge-discharge capacities, initial coulombic efficiencies as well as the specific surface area of NETO-x samplesx Discharge capacity / (mAh · g-1) Charge capacity / (mAh.g-1) Initial coulombic efficiency / % Specific surface area / (m2·g-1) 1 h 105.2 210.5 49.98 2 3 h 121.9 246.5 49.45 4 6h 143.5 282.2 50.85 7 12 h 187.4 358 52.35 1 24 h 144.2 295 48.88 1 在SEM测试过程中,我们还同时进行了样品的能量色散X射线能谱(EDX)分析,结果如图 6所示。根据EDX数据,3个样品中均含有Eu、Ti和O元素(H元素无法通过能谱仪检测到,因此存在的H元素含量无法确定),并且HNO3的处理对其强度有轻微影响。而Na元素的强度随着酸处理时间的增加而显著降低。当酸洗时间为6 h时,Na的信号几乎消失。这些结果表明Na+和H+的离子交换在处理6 h后基本完成,其结果与XRD结果对应。
图 6
图 7
为了验证酸处理使NETO中的Na+被交换出来,我们对酸洗液中的Na+和Ti4+进行了ICP测试,如图 7a所示。从NETO组成式中可以计算出,如果Na+完全交换出来,则溶液中的Na+浓度应为0.04 mol·L-1。从测试结果可以看出,在酸处理6 h后溶液中的Na+浓度为0.034 2 mol·L-1(为初始浓度的85.5%)。当酸处理12和24 h后,溶液中的Na+浓度分别为0.036 3和0.037 3 mol·L-1,是初始浓度的90.7%和93.3%。排除可能存在的误差,我们认为酸处理12 h后已经将NETO中的Na+基本交换出来。酸处理剩下的溶液中也检测到了Ti4+的存在。我们随后计算了不同酸处理时间下酸洗液中Na+与Ti4+的物质的量浓度比值,结果如图 7b所示。在酸处理开始后,酸洗液中cNa+/cTi4 +>10,6 h之后酸洗液中降至5以下。
这一结果表明,在酸洗处理NETO过程中存在着Na+-H+离子交换和溶解2种反应。在酸洗处理前6 h内,Ti4+的相对浓度缓慢增加,表明主要反应是Na+-H+离子交换;超过6 h后,Ti4+的相对浓度快速升高,结合晶粒形貌的变化,我们认为,此时溶解反应居于主要地位。
图 8显示了NETO和酸处理6和12 h后样品的1H MAS NMR谱。可以看到酸处理前后的样品均在6.2和2.1出现一个较强峰和一个较弱峰(如图 8中“*”所示),这2个峰应该来源于材料表面吸附的水[29]。在酸处理6 h之后,位于14.4处出现了一个新的峰,说明酸处理后出现了除吸附水之外新的氢质子状态,且没有出现属于结晶水的OH-峰(应该位于12.2处)[26],所以我们认为H+成功交换进入NETO晶格中形成HETO。另外0.4和-0.3处2个峰可能源于酸洗过程中由乙醇引入的氢。在酸处理12 h后,14.4和0.4两个峰向低角位移(~0.7)到13.7和-0.3,低角位移意味着产物中氢的电子密度相对较高[27],暗示着离子交换反应基本完成。
图 8
2.2 电化学性能
图 9显示了不同酸处理时间所获样品的循环性能。所有电池均在0~3 V的电压范围内以100 mAh·g-1的电流密度进行充放电循环。NETO材料的起始比容量为150 mAh·g-1,并在接下来的循环中迅速衰减,在170次循环后仅为50 mAh·g-1,由于其电化学性能很差,所以不再对其进行深入分析。经过300次循环后,NETO-1 h、NETO-3 h、NETO-6 h、NETO-12 h和NETO-24 h样品的可逆容量分别为165.7、166.9、190.7、213.2和199.3 mAh·g-1。其中NETO-12 h样品表现出最佳性能。由于H+和Li+交换程度加深,可逆容量在最初的几个循环上升后趋于稳定。我们计算了这5种材料在10~300次循环中的容量保持率,NETO-1 h、NETO-3 h、NETO-6 h、NETO - 12 h和NETO - 24 h的容量保持率分别为109%、109.1%、114.7%、117.9%和117.9%。在诸如Co3O4和ZnMn2O4的其他材料中也已经报道类似的容量上升现象,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循环过程中电极材料的表面形成了能够存储锂的SEI层[30-31]。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反应过程中带来的晶粒破碎化导致与电解质的接触面积增加所致[32]。
图 9
图 10中给出了不同酸洗时间后样品的初始充放电和第100次充放电曲线。该图表明所有样品均具有良好的电化学活性。表 1总结了它们的初始充电和放电容量,以及它们的初始库仑效率。当酸处理时间从1 h增加到12 h,首次充电和首次放电容量都会增加。首次充放电的库仑效率也通常会提高。而且,酸洗时间越长,放电容量越高。但是,经过24 h的酸处理后,其放电容量急剧下降至144.2 mAh·g-1。从SEM和TEM图可知颗粒的结晶度受到严重破坏,这可能导致容量下降。此外,所有样品的初始充放电曲线均有位于约0.8~0.9 V的平台,这应该对应于锂在晶格中的嵌入和脱出[15-16]。
图 10
仔细观察图 10发现,当处理时间超过3 h后,其初始充电曲线中出现一个接近1.5 V的新平台。在随后的周期中,该平台消失。文献[17]也观察到这一现象,并将这个平台归因于晶粒表明SEI膜的形成过程。此外,随着处理时间延长至6 h,其容量会略有增加,然后略有下降。这种变化与上述比表面积的变化相似,因此我们认为源自此平台的电荷容量增加归因于酸洗导致材料的比表面积的增加。
图 11给出了NETO和NETO - 12 h的Eu3d和Ti2p XPS谱图。由图可知,在1 164.6和1 134.5 eV处的Eu3d特征峰分别对应于Eu3+3d3/2和Eu3+3d5/2。Ti2p的3个主要峰位于463.4和457.6 eV处,分别对应于Ti4+2p1/2和Ti4+2p3/2状态。2个样品的Ti2p XPS谱图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表明酸处理并没有影响Ti和Eu元素的价态。
图 11
图 12给出了酸洗后样品前3次的CV曲线。所有样品的CV曲线均在0.70/0.98 V附近显示出一个耦合峰,这与脱/嵌锂过程中的Eu3+/Eu2+氧化还原对相关,与先前报告的结果一致[19, 33]。
图 12
关于充电-放电机理,我们认为NETO在酸洗过程中,Na+被H+置换形成HETO。在初始充电过程中,H+又通过电化学过程被Li+置换变为LiEuTiO4。然后,Li+在LiEuTiO4和Li1+xEuTiO4之间进行可逆的脱出和嵌入,如方程式(1)和(2)所示[15, 17, 34-35]:
$ \mathrm{H}_{x} \mathrm{EuTiO}_{4}+x \mathrm{e}^{-}+x \mathrm{Li}^{+} \rightarrow \mathrm{Li}_{x} \mathrm{EuTiO}_{4}+x \mathrm{H}^{+} \quad(0 \leqslant x \leqslant 1) $
(1) $ \mathrm{Li}_{x} \mathrm{EuTiO}_{4}+y \mathrm{e}^{-}+y \mathrm{Li}^{+} \rightleftharpoons \mathrm{Li}_{x+y} \mathrm{EuTiO}_{4} \quad(0 \leqslant y \leqslant 1) $
(2) 为了证实这种推测,我们对循环300次后的电极进行了非原位XRD测试,结果如图 13所示。经过300次循环后的电极其XRD图与LETO的标准图主峰一致[33],说明我们推测的充放电反应机理是合理的。
图 13
有趣的是,电池经过300次循环后,SEM图显示颗粒的表面损伤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自我恢复,如图 14所示。我们认为,由于Li+的半径大于H+的半径,当Li+将H+取代后,裂纹的宽度随之变小,同时,循环过程中形成的SEI膜也在一定程度上填充到裂缝中,使晶粒表面展现出表面损伤自行修复的现象。
图 14
图 15显示了不同时间酸处理后样品的倍率性能。所有电池均以100~2 000 mA·g-1的电流密度放电。其中NETO-12 h样品展现出最佳的倍率性能。在100 mA·g-1的电流密度下,NETO-12 h的平均可逆比容量为193.2 mAh·g-1;当电流密度提高到1 000 mA·g-1,其平均可逆比容量可保持在149.4 mAh·g-1;当放电电流密度恢复至100 mA·g-1时,NETO-12 h样品仍可保持193.6 mAh·g-1的可逆放电容量,并具有极佳的循环性能。
图 15
3. 结论
综上所述,NETO存在着Na+→H+→Li+的离子交换路径,即NETO中的Na+可以跟稀酸中的H+发生离子交换。交换后得到的化合物HETO可以在电池中通过电化学反应的方式转化为LETO。通过这样的路径得到的LETO与文献中报道的LETO具有同样优异的电化学性能。本研究有利于利用较为快捷的软化学方法来设计和筛选稀土基钛酸盐电极材料,同时可将NETO作为一种锂离子筛来进行锂的提取和回收。因此,继续深入地研究NaLnTiO4等具有层状钙钛矿结构材料的离子交换行为及电化学特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
-
[1]
Goodenough J B, Park K S. J. Am. Chem. Soc., 2013, 135(4):1167-1176 doi: 10.1021/ja3091438
-
[2]
Rao Z H, Wang S F. Renewable Sustainable Energy Rev., 2011, 15(9):4554-4571 doi: 10.1016/j.rser.2011.07.096
-
[3]
Yang Y L, Hu X S, Qing D T, et al. Energies, 2013, 6(5):2709-2725 doi: 10.3390/en6052709
-
[4]
Armand M, Tarascon J M. Nature, 2008, 451(7179):652-657 doi: 10.1038/451652a
-
[5]
Zier M, Scheiba F, Oswald S, et al. J. Power Sources, 2014, 266(15):198-207 doi: 10.1016/j.jpowsour.2014.04.134
-
[6]
黄可龙, 张戈, 刘素琴, 等.无机化学学报, 2006, 22(11):154-158 http://www.wjhxxb.cn/wjhxxbcn/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061126HUANG Ke-Long, ZHANG Ge, LIU Su-Qin, et al. Chinese J. Inorg. Chem., 2006, 22(11):154-158 http://www.wjhxxb.cn/wjhxxbcn/ch/reader/view_abstract.aspx?file_no=20061126
-
[7]
Ding F, Xu W, Graff G L, et al. J. Am. Chem. Soc., 2013, 135(11):4450-4456 doi: 10.1021/ja312241y
-
[8]
Zhao B, Ran R, Liu M, et al. Mater. Sci. Eng. R, 2015, 98:1-71 doi: 10.1016/j.mser.2015.10.001
-
[9]
Zhang B, Liu Y, Huang Z D, et al. J. Mater. Chem., 2012, 22(24):12133-12140 doi: 10.1039/c2jm31308a
-
[10]
Erickson E M, Ghanty C, Aurbach D. J. Phys. Chem. Lett., 2014, 5(19):3313-3324 doi: 10.1021/jz501387m
-
[11]
Clark S J, Wang D, Armstrong A R, et al. Nat. Neurosci., 2016, 7:10898
-
[12]
Yersak T A, Yan Y F, Stoldt C, et al. ECS Electrochem. Lett., 2012, 1:A21-A23 doi: 10.1149/2.014201eel
-
[13]
Wu K Q, Wang D J, Lin X T, et al. J. Electroanal. Chem., 2014, 717-718(15):10-16
-
[14]
Fan S S, Yu H T, Xie Y, et al. Electrochim. Acta, 2018, 259:855-864 doi: 10.1016/j.electacta.2017.10.203
-
[15]
Song S H, Alonso J A, Cheng J G, et al. J. Solid State Elec-trochem., 2014, 18:2047-2060 doi: 10.1007/s10008-014-2432-0
-
[16]
Song S H, Ahn K, Kanatzidis M G, et al. Chem. Mater., 2013, 25:3852-3857 doi: 10.1021/cm401814z
-
[17]
Huang J, Yang K H, Zhang Z X, et al. Chem. Commun., 2017, 53:7800-7803 doi: 10.1039/C7CC03933F
-
[18]
Wei D, Tang Q J, Tong D G. J. Taiwan Inst. Chem. Eng., 2019, 96:223-228 doi: 10.1016/j.jtice.2018.11.014
-
[19]
Toda K, Kurita S, Sato M. J. Ceram. Soc. Jpn., 1996, 104(1206):140-142 doi: 10.2109/jcersj.104.140
-
[20]
Geselbracht M J, White H K, Blaine J M, et al. Mater. Res. Bull., 2011, 46(19):398-406
-
[21]
Jacobson A J, Johnson J W, Lewandowski J T. Inorg. Chem., 1985, 24(23):3727-3729 doi: 10.1021/ic00217a006
-
[22]
Ruddlesden S N, Popper P. Acta Crystallogr., 1957, 10(8):538-539 doi: 10.1107/S0365110X57001929
-
[23]
Chiba K, Ishizawa N, Oishi S. Cheminform, 1999, 30(40):1041-1044
-
[24]
Bednorz J G, Muller K A, Takashige M. Science, 1987, 236(4797):73-75 doi: 10.1126/science.236.4797.73
-
[25]
Tezuka K, Hinatsu Y, Masaki N M, et al. J. Solid State Chem., 1998, 138(2):342-346 doi: 10.1006/jssc.1998.7794
-
[26]
Nishimoto S, Matsuda M, Miyake M. J. Solid State Chem., 2005, 178(3):811-818 doi: 10.1016/j.jssc.2004.12.033
-
[27]
Akimoto J, Chiba K, Kijima N, et al. J. Electrochem. Soc., 2011, 158(5):546-549 doi: 10.1149/1.3562207
-
[28]
Toda K, Kameo Y, Kurita S, et al. J. Alloys Compd., 1996, 234:19-25 doi: 10.1016/0925-8388(95)01969-3
-
[29]
Mangamma G, Bhat V, Gopalakrishnan J, et al. Solid State Ionics, 1992, 58:303-309 doi: 10.1016/0167-2738(92)90132-9
-
[30]
Anh L T, Rai A K, Thi T V, et al. J. Mater. Chem. A, 2014, 2(19):6966-6975 doi: 10.1039/C4TA00532E
-
[31]
Reddy M V, Subba Rao G V, Chowdari B V R. Chem. Rev., 2013, 113(7):5364-5457 doi: 10.1021/cr3001884
-
[32]
Wang L, Yu Y, Chen P C, et al. J. Power Sources., 2008, 183(2):717-723 doi: 10.1016/j.jpowsour.2008.05.079
-
[33]
Gupta A S, Akamatsu H, Strayer M E, et al. Adv. Electron. Mater., 2016, 2(1):186-196
-
[34]
Perez-Flores J C, Baehtz C, Hoelzel M, et al. Cheminform, 2012, 43(26):3530-3540
-
[35]
Chen Y X, Zhu D C, Ji C X, et al. Ionics, 2019, 25:3041-3050 doi: 10.1007/s11581-019-02864-2
-
[1]
-
表 1 NETO酸处理样品的初始充放电容量、初始库仑效率和比表面积
Table 1. Initial charge-discharge capacities, initial coulombic efficiencies as well as the specific surface area of NETO-x samples
x Discharge capacity / (mAh · g-1) Charge capacity / (mAh.g-1) Initial coulombic efficiency / % Specific surface area / (m2·g-1) 1 h 105.2 210.5 49.98 2 3 h 121.9 246.5 49.45 4 6h 143.5 282.2 50.85 7 12 h 187.4 358 52.35 1 24 h 144.2 295 48.88 1 -

 扫一扫看文章
扫一扫看文章
计量
- PDF下载量: 4
- 文章访问数: 2167
- HTML全文浏览量: 414

 下载:
下载:














 下载:
下载:

